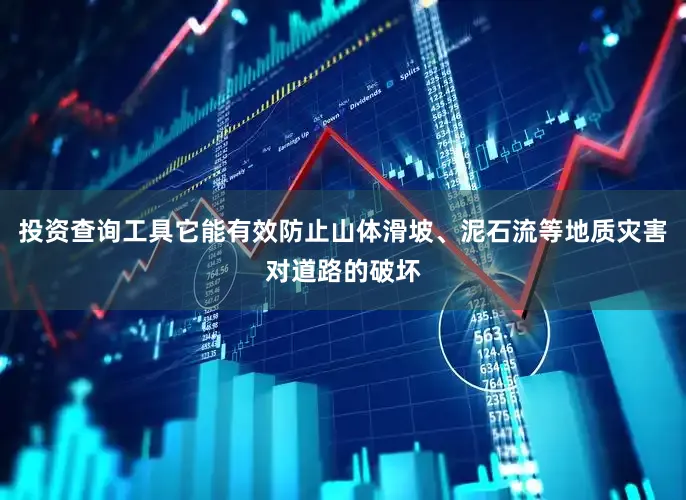李开元(章静绘)
今夏,秦汉史家李开元先后推出两本新著——《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7月出版)与《刺秦:重新认识秦王朝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2025年8月出版,以下简称《刺秦》)。前者是李开元的随笔,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剧本等不同类型的作品。后者系《秦谜:重新发现秦始皇》一书的姊妹篇,李开元继续深读《史记》,从历史记述之幽微处抽丝剥茧,重新发掘荆轲刺秦王这一经典故事,对其中秦汉史诸问题展开论述。特别的是,《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》中有两篇谈“历史时间”的文章,涉及对“历史是什么”的思考,而李开元在《刺秦》中由“如果荆轲杀了秦王”这一历史假设深入他的“侦探”之旅,那么,“如果荆轲杀了秦王”这一假设在李开元的“历史时间”之中吗?如何从历史假设推理出的叙述中重新认识秦王朝?这即是这篇专访的起点。
作为读者,我以为在解码刺秦的故事中能发现夏无且是“荆轲刺秦”这个故事的口述者,特别妙。而能揭示这一点在于您发现了《史记》中第二处关于夏无且的记载。那么,这一发现是出于偶然吗?或者说,司马迁面对不同的材料、不同版本的传说,他记《史记》时是否有意识地对这些信息进行呈现或交代?
展开剩余91%李开元:我们今天写作会明确地说是根据什么史料来写,把它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时并不是这样。他用了一些战国时期流传的材料,还有一些他听到的故事,他把这些笼统地合在一起,并没有告诉读者他具体是怎么做的。也正因为这样,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题,使我们能够重新侦查,有机会重新发现夏无且。
在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,夏无且出现了两次——第一次是在荆轲刺秦的现场,他用药箱去打荆轲,没中;第二次是事后秦王特别表扬他,说要赏赐他。这个细节一直以来都不太被重视,实际上我也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夏无且的人,顾颉刚先生就觉得这个人物很有意思,与荆轲刺秦的故事关系密切。《史记》中关于夏无且的第二处记载是在《刺客列传》的“太史公曰”中,司马迁在这里感慨说:世间流传一种谣言,说荆轲把秦王刺伤了,这是靠不住的。因为夏医生(即夏无且)在场,夏说没有刺伤,夏又把这个事情讲给公孙季公、董生听,他们两人又讲给我(司马谈,司马迁的父亲)听。所以,司马迁在这里把这个事情的前后讲了一遍。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推想的空间。
为什么以前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,是因为我们往往觉得秦汉之间隔得很远,没有注意到夏医生是生活在秦汉两个时代的人。事实上秦始皇死了三年之后,秦朝就灭亡了,又过了五年汉朝就建立了。夏无且一直活到西汉初年,我们可以推想,他在西汉继续做医生的时候可能会讲这个故事,这样一来,荆轲刺秦这个故事的流传脉络就清楚了。
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之所以精彩,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口语和动作的成分,精彩到让人觉得难以相信,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根据故事中的口语和动作的记载认为,这更像一出戏剧。他觉得是司马迁去看戏,看戏的时候把它记了下来。这些在书中,我都有谈到。我只是进一步修正说,夏无且作为刺秦故事的在场者,他后来口述了这个故事,故事中的口语和动作,都是他在场的耳闻目见,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文本。
《刺秦:重新认识秦王朝》,李开元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2025年8月出版
如果没有《刺客列传》“太史公曰”这一段,“夏无且是刺秦故事的口述者”还能成立吗?是否还有别的依据能证明这一点?
李开元:如果没有这一段,可能就是一半成立。
如果仔细解读荆轲刺秦的文本,一方面,我们可以发现夏无且两次出现。另外,还可注意到文本中的讲述是基于医生的眼光。荆轲刺秦是如何刺的?故事说荆轲左手抓衣袖,右手持刀刺过去,没刺到,秦王拔出剑后,首先砍断了荆轲的左大腿,总共砍了八刀,这些都是医生的眼光。因为医生要验伤,他就记得很清楚,都是很独特的视角。如果我们以很专业的眼光来看的话,可以看出来夏无且在这个故事中非同寻常,但是无法证明刺秦的故事是基于夏的口述。
关于秦始皇的相貌性格,您认为他身材高大、相貌堂堂、精力智力超凡,总之形象是比较完美的。您在书中阐明秦王猥琐、阴鸷的形象其实来自范蠡说勾践的相貌性格,并简单提及这与汉文帝时期的方士有关。这里可以展开谈谈吗?
李开元:以前帝王的相貌是忌讳,不能讲。而《史记》中有一段尉缭子见秦王的故事,专门说了秦王的相貌性格,但那个话很奇怪。尉缭子说秦王不可交,因为他“蜂准,长目,鸷鸟膺”,就是说鼻子如同野蜂,长眼睛,胸部如同猛禽,向前突出,说这种相貌的人有求于你的时候,他会低声下气,一旦他得意了就把你吃了,所以他坚决要走。这是有关秦始皇相貌性格的唯一的记载。
但分析这个故事之后,我认为是靠不住的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时会选一些他听到的故事放进来,有的是有根据的,有的就有问题。尉缭子见秦王的故事来自古代的相面术。大概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东汉,相面术都很流行——就是根据性格来推相貌,或者根据相貌来推性格,各有相应的类型。尉缭子说秦王的面相就属于当时相面术的一种类型,猛禽相貌约等于忍者或者狠人性格,一个典型代表就是勾践。
范蠡文种辅助勾践成功以后,范蠡就告诉文种,说我准备走了,这就说到了勾践的相貌属于猛禽相,可以共患难,不可共富贵,你不走就会被他杀了。文种的结局果然被范蠡说中了。所以,尉缭子对秦王相貌的描述,其实也是相面术的一种相似类型。而且,仔细研究尉缭子这个人,他根本不可能见过秦王。所以,这个故事可能是后来人的添加,并非出自司马迁的记载。
在荆轲刺秦的故事中,我们看不到秦王的相貌,但可以推想他的体魄,应该是很敏捷、健硕的。他跪坐案前,面对荆轲的刺过来的剑,他可以一下跳起躲避,荆轲还追不上他,说明他腰腿力量都很强,绝无大腹便便的累赘。再考虑到他的父亲是秦国王子、母亲是赵国的舞蹈演员,这样的基因组合,正常情况下,应当不会差。
秦始皇年轻时曾经受过很多委屈,但功成之后,没有无辜诛杀过任何一位功臣,这说明他性格比较沉稳宽容,并不因猜忌而乱杀人,他的相貌不应该是勾践这个类型。那更接近的是谁呢?我认为是东汉的光武帝,他不诛杀功臣,性格沉稳宽容。如果我们也从相面术的角度从性格推想相貌的话,秦始皇应当与光武帝属于同一龙相类型,“虎口日角,大目隆鼻”,也就是有力的大嘴,前额隆起,大眼睛高鼻梁。古代类书《太平御览》中有这样一条材料。当然,这也是基于相面术的推想,真相还埋藏在秦始皇陵下面,留待将来。
那么,对于秦始皇相貌的这种曲解是如何形成的呢?是因为秦汉更替而对其的抹黑吗?
李开元:有这个原因,但时间比较晚。
汉初,刘邦对秦始皇是非常尊重的。刘邦对以前的帝王,比如说各国的国王,包括信陵君都很尊重。他还曾拜祭秦始皇陵,为他设置的守墓专业户最多。为什么如此?因为最初刘邦他们觉得汉是继承了秦的,刘邦是以秦为根据地统一天下的。但文帝晚年的时候就出现了改制的动向,从贾谊开始。他们认为,我们不是秦的继承者,而是革命者,于是鼓吹改制的方士们制造了很多舆论,编造了很多故事,包括秦始皇的相貌。这点我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,但是觉得最可能是在这个时候。当然,文帝时并没有成功实现改制,到汉武帝时最终实现了改制。所以,方士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经过一段时间完成的。
另一方面是司马迁的态度。司马迁是秦国人,他祖上曾是秦国很重要的官吏,他对秦是有感情的,评价也比较客观。他对秦始皇有很多批评,认为统一天下是伟大的事业,而统一以后继续对外扩张,劳民伤财,这是秦亡很重要的原因。但是《汉书》的作者班固可不同。班固是楚国人。楚国被秦灭亡以后,把他们强制迁徙到了山西北部去,他对秦是有家仇国恨的,所以包括像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样的说法,都是从班固开始的。
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史记》不是司马迁的原著,而是在流传过程中被掺入了很多东西之后的版本,而其中的“加工者”就有班家。因为《史记》比较特殊,长期以来是禁书,不许在外面流传,直到东汉末年以后,才开始公开。所以,在秦汉简大量出土的今天,我们从来没有出土过《史记》。
回到刺秦的故事。李斯入狱后为自己请功摆好时,为什么没有把他最重要的三件功绩列上去,您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?
李开元:以前大家都没有注意到,李斯在狱中上书的时候为自己评功摆好——这个材料来源比较清楚,因为《史记》里有这个事儿,出土的《赵正书》里也有这个事情,两相比照,就发现司马迁把《赵正书》里最常识性的错误都改了。所以我们就有个推论:司马迁是看过《赵正书》的,他选取了这个故事,修改后放进《史记》中。
我对李斯的评价很差,我觉得他是秦亡的三大罪魁祸首,另外两个是赵高和胡亥。李斯的品质极坏,完全不讲道德,只讲利益,所以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站在自身的利益上出发。废封建行郡县这个事儿,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在边疆应该实行双轨制,而李斯看准了秦始皇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点权力,所以独排众议坚持要行郡县,就像他看准秦二世既想治国又想享乐的心思,所以设计一个万全其美之策一样。这个人非常利己,只看重自己的利益。
李斯为自己评功摆好所列举的几件事,我们仔细看,大部分都不是他的功劳而是秦的国策,还有他瞎说的,比如打匈奴,他本是反对的,现在说成支持。而他最光彩的事情——主张废封建,彻底地行郡县,这是他独排众议实现的,却绝口不提。为什么?我想这个人很聪明,他已经明白郡县制引起了秦国极大的问题,这是秦速亡的一个原因。然后,他主张焚书,引起文人的集体反抗,他也不提。《谏逐客书》他也没有提,因为《谏逐客书》涉及他对秦国贵族的抵制和排斥。所以说,他之所以没有提,是因为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三件事提出来就是错误。
顺便提一句,最近,也有学者怀疑李斯狱中上书不是他自己写的,可能是汉朝人伪造的。不过,在质疑旧说而没有新说建立的情况下,沿用旧说依然是一种较优的选择。
在秦的外戚斗争中,秦始皇是什么样的角色?
李开元:秦始皇从一开始就直接受到三种势力:一个是楚系,这是最强大的,从宣太后到华阳太后,一直到昌平君;另一个是韩系,来自他的亲祖母;还有一个即赵系,来自他的母亲,嫪毐就属于这一系。对于这三系势力,秦始皇最早清除的是韩系外戚,从打击异母弟成蟜入手,最大的功臣是嫪毐,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始皇的母亲赵姬,嫪毐由此就膨胀起来了。在秦始皇正式继位的时候,发生了嫪毐之乱,镇压嫪毐之乱后,赵系势力被清除。如此一来,楚系一家独大,等华阳太后去世以后,秦始皇就利用这个机会把楚系势力排除在外。
在清除外戚势力的斗争中,秦始皇清除韩系外戚势力,借助赵系外戚势力,主要是借助母亲帝太后和嫪毐的力量。清除赵系外戚势力,借助楚系外戚势力,主要是养祖母华阳太后和昌平君的力量。华阳太后去世后,将昌平君免相,排斥所有的外戚和王族,重用如同蒙氏家族和李斯赵高这样的贤人,实现了国君个人专权。
《谏逐客书》就是讲要任人唯贤,不要用任何亲信,包括贵族、王族、后族,但这些本就是秦国政权稳定几百年最重要的因素。排斥了这些人之后,如同李斯、赵高这样的无德贤人就逐渐冒出来了,他们当然有才,但是会无序野蛮膨胀,甚至取代你。所以,应该是亲贤并用,用亲族以稳定组织,用贤才以开拓进取。因此,到了西汉初年,刘邦实行的是双轨制,明确提出亲和贤并用,封建和郡县并行,这样他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基础,才能够延续。
《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》,李开元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7月出版
《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》中有两篇关于历史时间的文章,这是您什么时期的思考?
李开元:二十年前。那时候我有一个梦,准备写一本《历史学原理》。因为我喜欢哲学,喜欢罗素,看了罗素的《数学原理》很佩服,就想写本书把历史学究竟是什么讲清楚。我做了很多尝试,比如从光学的角度,从信息论的角度解读,后来都失败了。之所以失败,有一个原因是找不到表现思想的形式。有些问题已经考虑过了,但找不到表现的形式,论文这种形式肯定不行。于是就尝试以最调侃的语调、最不正经的形式来阐述一下我当时是怎么想的。前后写了五篇文章,投给《读书》,《读书》不接受,我也不打算改,就这样搁下了。
这五篇里就有谈历史时间的文章,一篇是《开源巴赫猜想:说历史学时间》,一篇是《千禧年在何年:说历史学时间的虚拟起点》。我觉得历史学的时间跟我们平时理解的时间不同。我们现在习惯以为时间是客观的,方向是过去—现在—未来。实际上并非如此,时间是一种人为设定的观念。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,时间成了历史学的基本要素。不过,历史学者用了一种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时间观:现在—过去方向的时间。就像考古的地层一样,我们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去挖,先看到民国,然后是清代、明代……从现在到过去,倒序去挖去看。不过,从现在到过去进入历史后,必须确定一个观察点,然后再顺着从过去到现在的方向重新观察和书写历史。比如我们研究秦朝,首先从现在出发,倒过去进入两千年前的秦朝。进入秦朝后,选定某一起点(虚拟时间点),比如秦王政即位的前246年,然后从这个时间点,再顺序来观察和书写秦国的历史,从秦王政到秦始皇到秦二世——从过去到现在。
所以说,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时间观是很奇特的,是从现在回到过去以后,又从过去到现在重来。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。这种从现在到过去,又从过去到现在的认识方式,可能是历史学独有的?当然,这种探讨,一般人觉得太抽象不好理解,历史学家也多不关心,难得你关心到这个问题,我就多说两句。
如何在这个时间理论上理解历史假设?
李开元:从历史学时间观的角度看,假设就是一个虚拟时间点的选择问题。为什么说历史可以假设?以荆轲刺秦王来说,就在于我选取什么样的观察点。如果我选的观察点在荆轲刺秦以前,他就可能失败,也可能把秦王杀死,这就自然会引出如果荆轲刺死了秦王,历史会如何演变的历史假设了。如果选择的观察点在荆轲刺秦完成以后,那么就只能接受荆轲刺秦王失败,进而再做分析。
一般而言,假设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。假设就相当于我们语言里面的“如果”。科学研究多是从假设开始,先假设再证明,我认为在历史学里完全可以假设。当然,假设分有价值的假设和没有价值的假设。我在《刺秦》里做的不是反事实的假设,而是在假设里找到一些真事实。以荆轲刺秦来说,太子丹的预定方案——首选是挟持秦王以实现他们的诉求;其次才是刺死秦王。那么,我们在这个历史时间上假设如果当时执行了第二套方案,那么,刺死秦王会发生什么?对此太子丹有预言:“大将在外”,我分析是指王翦带着大军在外面,“内有内乱”,那么从外戚的线索看,就是昌平君等楚系人物登场。这样历史就活了,这个假设就是有价值的假设。
不同于大多数历史学者,您在很多其他领域进行了史学的实践,比如电影、舞剧等等,跟不同领域的人接触,您对历史有什么新思考?
李开元:领域和领域不一样,碰撞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比如,我在书中提到“王负剑”的问题,就是电影导演陆川在拍电影的时候,他深入历史现场,他要复原当时的场景,就提出了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,过去做历史研究的人多没有关注到。这个事儿提醒我去思考,想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深入追究下去的结果,得到了文物专家孙机先生的精准解答,他有一篇很著名的论文讲古代中国的佩剑法,叫做璏式佩剑法,完美地解释了“王负剑”。
这给我们的提示是,历史学者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书斋里,那容易把自己禁锢在一些固化的框框里,看不见活生生的历史。我们的历史遗产有各种各样的功用。它是一种学术资源,可以供专家去研究,它也是一种教育的资源、旅游的资源,甚至是一种娱乐的资源,这不是谁能独占的东西。深入到历史资源的不同使用领域中,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提示。
由此引申出来的另一个课题是,历史学的定义,可能需要重新修正。近百年来受科学主义的影响,我们习惯于接受问题研究才是历史学,历史研究就是写论文。而近代以前的历史学,都是叙事的。如今的历史学,放弃了叙事,研究一边倒。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,历史由谁来写?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白。很长一段时间是媒体人写历史,爱好者写历史,历史学家又不满意,很矛盾。
我写《司马迁来到B大历史系》,用了文化寓言的形式,想要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。呼吁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,“为历史学收复失地”。研究和叙事,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,历史学既要研究也要叙事,既要追求真也要追求美,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生动地把历史写出来。
发布于:上海市仁信配资-正规配资官网-股票可以杠杆-正规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配资的公司行业门户最怕人说他“搬弄是非”
- 下一篇:没有了